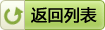|
真不好意思,我是研究生
查看(1531) 回復(0) |
|
|
發表于
樓主
我一直都不太愿意提起我的研究生學歷和碩士學位。這不是謙虛,是有點兒
心虛。 我是國家計劃內招生的全日制碩士研究生,可在實際工作中,我感覺不到自 己這個碩士比人家本科生高明到哪里去,雖然學校給我們制訂的培養目標是本專業內 的高級人才。 回想起研究生期間的學習,有很多遺憾。 在讀研之前,我對自己的研究生生活滿懷憧憬:即將就讀的學校和學科在國 內很有名氣,擁有一流的專家學者隊伍;研究生的學習非常自由,我可以大量選修自 己感興趣的課程,拓展知識結構;可以徹底擺脫記筆記、背筆記、考筆記那種學習模 式的折磨,跟討厭的考試、分數說“拜拜“。 可是一周的課上下來,我感覺又回到本科時代。 按規定,讀研的3年里,我們要修滿58個學分。可是在這期間,有一個學期 要實習,最后一年要做論文找工作,也就是說,大部分學分要在1年半的時間里修完 ,這就意味著我的時間幾乎要全部用在上課上。更不可思議的是,這50多個學分幾乎 都是必修課。 我們的課程由公共課、學科基礎課、方向專業課和方向選修課4部分組成, 前3部分是必修,而所謂的選修課,也是限制選修,必須得學。 對這樣的培養計劃,導師們也意見很大,認為課程太多,學生根本就沒有時 間讀書、做研究。可是意見歸意見,想法歸想法,培養計劃不變。 第一門課是公共課。我以為老師會布置一些書目,大家回來自己讀書。一上 課,發現還是老師講,學生記的老套路。看著老師在講臺上講得口干舌燥,同學在下 面低著頭匆匆記錄,與讀本科時并無兩樣,我感覺又回到了本科時代。 對專業課我也深深失望。首先,專業課課程設置和本科大量重復,沒有拉開 差距,連課程的名稱都差不多。本科學的是中國新聞史,現在叫新聞史研究;本科時 叫新聞編輯學,現在叫新聞編輯學研究。雖然后面加了“研究“,但內容沒有多少差 別,只不過細化了些。比如,新聞攝影研究,老師講的還是照相機的結構、成像原理 、感光片的種類這些基礎知識。中國新聞史研究,老師居然從新聞的起源講起。且不 說我這種專業出身的,就是那些跨專業學習的同學經過入學考試,對這些內容也已經 爛熟于胸。 不但如此,授課內容陳舊、老化,跟社會現實幾乎沒什么關系。人類已進入 21世紀,新聞傳播業已進入一個巨變的時代,可是學的課程中,有相當一部分課程還 在重復那些講了幾十年的東西。新聞評論學研究,關注的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些 政論家和他們的作品,時代背景、作品風格、寫作特點、主題思想不厭其煩。梁啟超 的評論確實寫得漂亮,我們應該有了解,可是花大量的時間去總結、記憶他的作品有 什么特點、是什么風格,有多大的實際價值呢?更何況,這些知識在新聞史的課堂上 ,在任何一本研究梁啟超的著作里都有論述。這種重復學習又有多大必要呢?新聞評 論和時代是緊密聯系的,為什么我們不去研究一下當代新聞評論新的發展趨勢和其承 擔的功能呢? 現在連中小學都提倡研究性學習,我們的大多數課卻還是以老師講授為主。 有一門課主要是介紹名記者和他們的報道作品,按說,這門課完全可以讓學生選擇自 己喜歡的記者進行研究,然后互相交流心得和成果,再一起研討,既鍛煉大家的科研 能力,又有思維的碰撞和交流。可是,這門課的教授方式還是老師介紹、學生記錄, 考試考筆記。 這種課聽起來不但乏味而且收獲甚少。到了第二學期,逃課的同學越來越多 。大家各忙各的,“出國派“時間用在考托考G上,“實踐派“整天忙著在外面兼職 打工,既鍛煉實踐能力,又解決生活費用。少數立志搞學術研究的同學,精力也沒放 在課堂上,而是轉移到了圖書館。 我開始失望,我問自己,讀研到底有什么意義,如果僅是為了一紙文憑,浪 費這3年的時光值不值得? 導師是什么,導師應該是引導我們走進學術研究之門的人,應該是經常能給 學生以指導的人,應該是經常與學生進行學術討論,學術切磋的人。可實際上,又有 多少人能從導師那里得到切實的指導呢?且不說導師自身的研究水平和能力如何,導 師有沒有時間和學生交流探討都成問題。 我的大學同學曉寒,在讀研究生的3年里,和導師的每一次交流都是逢年過 節在飯桌上進行的。曉寒的導師帶了一群研究生,自己又有行政職務,根本就無暇顧 及每個學生。有時候在外面遇見學生,拍著學生的肩膀連聲說“你好,你好“,卻叫 不上名字。 我有幸遇到了一位認真嚴謹的導師,還不時地抽查我的讀書筆記,或是要我 匯報生活和學習情況。不過,他老人家也經常感慨,“哎,事情太多了,沒有多少時 間管你,主要靠你自己學。想當年,我帶你大師兄時,每兩個星期就要談一次話。“ 最近,打電話問候導師,導師抱怨說,他現在帶的學生比我那時多了一倍,“到畢業 的時候,連每個人的論文認真看一遍的時間都不夠“。 近年來,我國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大,招生人數以每年30%的速度遞增。可是 研究風氣淡薄,研究生的思考能力普遍下降,卻已是不爭的事實。 按照培養計劃,每個學年我們都要寫一篇學年論文,這是培養科研能力的一 個重要環節,可據我所知,我們班有一半同學的學年論文都不了了之。我恰好當時幫 老師做了兩個課題,最后就當做了學年論文。 畢業論文,應該是檢驗學生是否達到培養目標的重要依據之一。可是現在, 畢業生論文大都是粗制濫造之作,既無新的創見,又無學術價值。 我一位師姐關于第四媒體的碩士論文被答辯委員評價甚高。你知道她用多長 時間寫的嗎?一個星期。她一直忙著聯系出國,哪有時間專注于論文,她是在網上找 的資料,“再找一個巧妙的角度,把材料組織好。“ 這位師姐說,答辯委員都是我導師親自請的,能為難我嗎?她還說,“他們 都不太了解因特網“。 那時,我對師姐的話半信半疑。直到自己走過一遍后,才知道,碩士論文, 真的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兒。 到了研三,大家忙著出國、忙著找工作,論文只能湊合。在校圖書館,我查 閱了不少學長的論文,有的水平真不敢恭維,簡直就是資料的堆砌,有些連錯別字都 沒有改過來。盡管如此,絕大部分論文都能順利通過。沒有哪位導師會卡自己的學生 。論文的評閱人和答辯委員一般都由導師選定,答辯時,答辯委員們也會提一些問題 、挑一些毛病,但最后的結果一定是“同意授予某某同學碩士學位“。在外面等候的 導師也就進來表示感謝,然后大家共赴學生準備好的宴席,皆大歡喜。 說實話,我們也想好好做一篇論文,畢竟是對自己3年研究生學習生活的總 結,可確實身不由己。我的論文著手比較早,開始也下了一些功夫。研三暑假一開學 ,我就天天泡在圖書館里查資料,也做了一些調研。但一個半月之后,隨著校園招聘 會的開張,我就踏上了求職路,論文只好暫時放下。 12月份,在導師的催促下,草草列了一個提綱,做了開題報告,但元旦前后 正是招聘高峰,幾乎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應付大大小小的招聘考試上,論文再次 擱置。 春節之后,工作還沒有著落,只好一邊參加各種考試,一邊寫論文,直到4 月中旬才把論文初稿交上去。這在我們班還算是比較早的,有位同學5月份才動筆, 論文的質量可想而知。 回想我的研究生生活,要說一點收獲都沒有也不客觀,自己的邏輯思維能力 、分析問題的能力還是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自認為和研究生的培養目標距離 很遠。我有自知之明,反正我不是什么高級專業人才。 看了這位研究生的信,我不由想起一個很久以前發生在美國校園的故事。 1908年秋天的一個早晨,正在哈佛讀二年級的李普曼,忽然聽到有人敲他的 房門。他打開門,發現面前站著一位銀須百發的老人。他愣住了,因為他發現這位老 人是哈佛最著名的導師--哲學家威廉.詹姆斯。 威廉.詹姆斯笑著對他說道:“我想我還是順路來看看你,告訴你我是多么 欣賞你寫的關于溫德爾的文章。“ 原來,李普曼在哈佛大學校刊上發表的一篇關于溫德爾的文章被威廉.詹姆 斯教授看到了,他是來向李普曼表達他的欣賞之情的。 從此后,大學二年級學生李普曼成了詹姆斯教授家的常客,每周四上午11點 ,他都來到教授家和他一起喝茶,他們妙趣橫生的談話涉及政治、社會、倫理宗教等 各個領域。和這樣的智者談話讓李普曼獲得了極大的鼓勵和精神上的收獲。他在給父 親的信中寫道:“這(與詹姆斯的談話)是我在哈佛的生活中最了不起的事情。“ 我還想起很久以前發生在北大校園的一個故事。 1918年的一天,兩個乳臭未干的年輕人傅斯年和羅家倫來到了大學者胡適的 家,與他探討“文學革命的種種主張“。剛開始時,兩個學生還“客客氣氣地向胡教 授請教“,后來熟悉了,師生之間的討論變得“最肆無忌憚“,常常爭論得面紅耳赤 。這種自由的討論和平等的對話,給當時的傅斯年等人帶來極大的影響。這以后,他 們與胡適保持了終生的友誼。 說到北大,還想起了那位錚錚鐵骨的馬寅初校長。聽說他當年對學生講話時 ,常用“兄弟“自稱,把自己與學生看作平等的交流對象,甚至可以與學生一起喝酒 罵人。 這些故事透露出一種久違的信息--大學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聯合學生和老師 共同對學問進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識和火熱的生活之間的關系。大學是傳授 知識的地方,但它是富有想象力地傳授知識,而決不應該是批發知識的場所。 正是由于缺少這種富有想象力地傳授知識的環境與氛圍,大學成了令許多年 輕人失望的地方。他們懷著熱望走進大學,潛心地尋找理想并時刻準備得到它,但是 他們從教師那里得不到多少有益的啟示,于是,他們中有的人感到理想的縹緲和希望 的破滅以致無所適從,有的人則隨波逐流、玩世不恭。 一位同仁問:你知道研究生究竟在研究什么嗎? 他說,我的一位讀研究生的朋友,一年級跳舞談戀愛,在興奮狀態中過了一 半,剩下一半時間用來對付幾篇學期論文,應付公共課考試。二年級跑到公司打工, 所從事的業務與專業毫不相干。大半年下來,一套行頭都換了,儼然一個小款。三年 級,慌慌張張準備論文開題報告,年剛過,又要出去為找工作奔忙。我問他,這樣過 ,哪有時間讀書、寫作?他不以為然地說,現在很多人都這樣,讀研不就是為了找個 好工作?搞什么研究?寫文章不都是東拼西湊,毫無價值的嗎? 不僅他,與他同一級的其他幾位研究生也是如此,大部分時間用來與書商合 作“攢書“,宿舍成了作坊,都三年級了還遲遲未能發表一篇學校規定的資格論文。 另外幾位則在拼命準備托福考試。…… 有人甚至尖銳地抨擊目下大學生是“有智商,沒有智慧;有前途,沒有壯志 ;有雄心,沒有烈膽;有文化,沒有教養;有知識,沒有思想;有眼光,沒有見識。 “而“碩士不碩,博士不博“,也似乎不足為怪。 上海學者許紀霖感慨地說:“我做了將近20年的大學教師,現在的博士研究 生,只相當于過去的碩士生;現在的碩士生只相當于過去的本科生。“ 正如一位學者指出的那樣,碩士學位本身已不再是學術有造詣的標志,而僅 僅意味著能過上一種收益可觀的生活。這無疑是高等教育的退化和悲哀。 今天,不難看到,在一群又一群應試高手和創新低能兒被批量生產出來的同 時,研究生教育所固有的理念和初衷也正在遭到破壞,無論是本科生、研究生,還是 博士生,他們又有幾人能無愧地說“我是合格的畢業生“。 他們也許誰都不想這樣混日子,誰都不想做一個腹中空空的人。但是為什么 大學校園里會彌漫著這種浮躁、淺近、輕飄的學風?為什么偌大的校園難以放下幾張 平靜的書桌? 那位學新聞的研究生羞于自己是研究生,一位剛走出大學校園的理工科學生 卻羞愧自己所受到的大學教育。 他說:“我的大學是一所理工大學,盡管校方在介紹里稱之為綜合性大學。 事實上是,我們除了應付考試,文、史、哲、經、法的書籍一概拒之門外。 大學“重理工輕人文“的程度遠超過我的想象,而且從校方到學生似乎也沒 人覺得有什么不正常。回想我4年的大學生活實在令我慚愧得無地自容。每一天都在 愚蠢地打發時間:背爛了的英語單詞一個也沒記住,寒冷的夜里無休止地自習卻依舊 什么也不懂。身邊的人更使我打不起精神來。 幾乎沒有人讀過《唐詩三百首》,也不曾讀過諸子的任何一家,盡管他們都 有很高的GPA;沒有人看過《莎士比亞戲劇》,也沒有人看完過《悲慘世界》,盡管 他們的“寄托“(GRE,TORFL)都考了很高分;沒有人看過《資本論》的一頁,也沒有 人讀完只短短幾十頁的《共產黨宣言》;沒有人傾心于安娜的高貴和反叛,也沒有人 為瑪格麗特黯然神傷。 我羞愧我所受到的大學教育:它不是塑造靈魂的教育,年輕的心根本無處探 索闖蕩,更談不上具備獨立的人格自由地觀察世界、思考世界。我只是被當做流水線 上的一個產品而整齊地按統一規格打造。年輕的頭腦毫無例外地被圈禁到麻木,喪失 激情。 我終會離開我的大學,而同樣的事情還在發生,同樣的悲劇還在繼續。“ 有人曾質疑,為什么中國幾十年的理科教育培養不出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 為什么中國的教育只能大批地培養“匠“,而很少能培養出“家“?一位留學德國的 馬來西亞華人,講了一個中國留學生兵敗德國考場的故事。 一位在國內接受了多年學校教育的中國學生,到德國留學后始終擺脫不了國 內那一套填鴨式的學習方法。有一回他去考試,考試內容是數學概率。考試前,他把 所有的計算方法一個不漏地學得滾瓜爛熟,幾乎沒有未曾做過的習題了,本以為可以 過關斬將,考取高分。誰知道不到5分鐘,他就垂頭喪氣地鳴金收兵了。 原來,教授畫了一個書本上完全找不到的概率分布圖給他(當然,這是教授 杜撰的,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這種分布),要他解釋是怎么回事。 他頓時暈頭轉向,啞口無言,只好對教授說:“您給我解一道數學題吧,我 就只會解題。“ 教授回答說:“那你可以走了。“ 上海復旦大學一位教授去斯坦福大學講學時,曾故意住進學生宿舍。他看到 ,每天下午5點以后,宿舍大樓底層的活動大廳就開始熙熙攘攘,有彈鋼琴的,有唱 歌的,有打橋牌的,但更多的是在閑扯(他們叫作“chat“)。在與學生的接觸中他發 現,那些學生并不非常用功,但接受和分析新鮮事物的能力很強,很多同他們所學專 業毫不相干的事情,略加解釋,就會體會其主旨。這是因為,從小學一直到大學,學 校給予他們的是認識、觀察和思維的能力,而不是靠記憶獲得的死知識。 在今天這個越來越國際化的社會里,我們確實有必要向四周張望,確實有必 要知道別人是怎么做的。讓我們看一看幾位歸國博士眼中不同國家的高等教育: “在美國,他們比較注重自學。教師講的內容與教材上的差異很大。 本科生可以以科研助教的身份出入一流的實驗室或研究中心,同教授們廣泛 進行交流;根據個人的興趣,那些雄心勃勃的高材生們可以自行提交研究報告,在學 者們的指導下,以合作或單獨進行的方式展開研究,最終,個人研究成果經過相應的 評價考核后,學生取得不同的學分。 在碩士研究生這個層次上,他們很重視寫,一般說來,每周看完閱讀材料后 要寫5-10頁的小論文。如果是比較大的討論課程,每學期至少要寫兩篇25頁左右的論 文,主要是對所讀文獻進行評論,提出自己的見解。理工科學生大部分時間泡在實驗 室,實驗完后,要寫實驗報告。 到博士這個層次,上課時大部分時間用來討論,教授的作用是引導,討論主 要是讓你對讀過的內容提出看法,作出批評。“ “日本的大學是通才教育,他們更注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從大學三年級 下學期到畢業,學生有一年半的時間都在實驗室,高校里有90%的實驗結果是學生完 成的,老師只是提供思路。日本學生在實習時,也不問什么實驗目的,理論依據,而 是跟著老師一塊操作,幾次實驗做下來,什么都會了。所以,日本的學生畢業后適應 性很強,什么樣的工作都可以干。“ “加拿大的高等教育,一般是寬進嚴出。比如招研究生,不經過考試,只取 決于兩個條件,一是你的大學成績,二是導師愿不愿意帶。在校內,大學生有較大的 自由度,選修還是必修由自己決定,但有個規定,學理科的必須選一門文科課程。“ 一位教育學者指出: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模式告訴我們,對復雜的 知識整合與應用的重要意義已遠遠超過對知識單純的記憶和梳理;而一種創造性的實 踐品格正依賴于所提供的教育環境。 (zz) |
|
回復話題 |
||
|
|
|
|